
在世人眼中,我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中年人:X世代的一员,中产阶级,顺性别、异性恋、行为举止符合社会期待的白人男性,居住在郊区。我在一家大型企业担任数字项目经理。我的业余爱好包括跑步,跑步时听播客,以及去当地的酿酒厂参加问答之夜,在那里,我常常以“我当时正在听一个播客……”来开启我的故事。
然而,若你在跑步时看到我身着无袖衫,或许会注意到我手臂上的纹身,上面刻着“Angel 1979-1998”。走进我的家,你可能会发现,在我家人的照片、我妻子的家人以及我们宠物的照片中,唯独没有我父母的身影。倘若问答之夜的谈话触及共同的童年经历,我或是无法感同身受,或是会分享一段我个人经历中扭曲的片段,而这往往让对方不知如何回应。 也正是在那段时期,真正的问题悄然浮现:我,一个拥有如此经历的人,又有什么资格去探讨如何建立一种道德的生活?
我必须亲身去经历,去赢取这份资格。
我的生命账本上,写满了亏欠。然而,关键在于,没有人能在孤立中累积亏欠。毕竟,如果没有偿还的对象,又何谈欠款?
起初,我曾是被亏欠的一方。我的童年本应是寻常的,却因父母不愉快的离婚而蒙上阴影。父亲带着我和我的双胞胎妹妹,告诉我们母亲是“抛弃了你们”。
随之而来的是贫困、动荡、家庭暴力,以及难以磨灭的创伤。我的父亲,他施加了切实的伤害。而那个袖手旁观的世界,则犯下了冷漠的罪。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十九年。然而,在这漫长的岁月中,亦不乏那些并非冷漠之人。他们不求回报,却积极地积累着信任,投入自己的力量。他们是我的邻居、教练、导师——那些选择看见我、见证我的人。 然而,我所选择见证的,仅限于那些曾加诸于我的伤害。十九岁那年,我心中充斥着愤怒。我愤恨那位已故的父亲,他留下了无数难以磨灭的伤痕;我愤恨那位抛弃我的母亲;我愤恨那些阻碍我掌握我本应拥有的未来的制度。那个未来,本该是我为童年付出的代价、逝去的天真、失去的快乐、破碎的完整而应得的补偿,一份理所当然的补偿。
然而,所有这些伤害之中,还有一个更甚。我的双胞胎妹妹在我十九岁那年离世。那段日子无比艰难,至今亦然。但那并非伤害。她的脑动脉瘤,并非任何人的过错。
伤害,是我自己造成的。
我的双胞胎妹妹……她的名字叫安琪尔。她的名字即是安琪尔。我知道,这名字似乎过于直白。她承受了我童年时所经历的全部伤害,甚至更多。但她面对世界,却不曾怀揣愤怒,也不认为自己理应得到什么。她以快乐、以力量,以及一种对生活的热爱去迎接,这份热爱即便在几十年后的今天,依然能轻易地让人嘴角上扬。而她将这份快乐传递给我,传递给他人,我敢说,无人能及。 她从未停止给予我爱,而我却习以为常,理所当然地全盘接受。毕竟,在我眼中,还有什么比我自身更重要?还有什么值得我为之驻足、为之关注?
她离世的第二天,我们的继母将我拉到一旁,告诉我:“这周我和安吉尔聊过,她很不开心。她觉得你从来没有真正关心过她的生活,没有给她机会分享她的点滴。她说她担心你不爱她。”
多年来,我一直被告知继母的话并非事实,我的双胞胎妹妹并非带着“我是否真的爱她”的疑问离开人世。然而,这个念头却并非空穴来风。我当然爱她,我对此深信不疑。但行动至关重要,言语同样不可或缺。而我,在这两方面都未能给予她应有的关注。 即使她曾有过一丝一毫的念头认为我不爱她,那也源于我言行举止的失当,是我无法弥补的伤害。那一刻涌上心头的内疚,以及我余生都必须为此付出的代价,正是促使我开始探寻“如何过上美好生活”的契机。
这场探寻由此催生了一系列深邃的问题:
“如果存在一位全能、全知、全视的上帝,为何世间仍有邪恶?”
“善与恶的界限究竟在哪里?”
“在这个充满伤害的世界里,我们彼此之间究竟亏欠着什么?”
这些问题并非在那一刻就完整地浮现于我的脑海,而是逐渐成形,在我心中扎根。
对于那些已然注意到“我们彼此亏欠什么?”这一特定命题的朋友们,甚好。我即将深入探讨此问题。 然而,首先,让我们思考一下“我们确实亏欠彼此,或者亏欠任何人任何东西”这一说法。我们真的亏欠吗?我知道很多人会争辩说他们不亏欠。他们会说,他们是靠着“全美式自力更生™”白手起家的,一切都靠自己,没有人给过他们任何东西。
你可能会对这种“红白蓝”式的稻草人论调嗤之以鼻。但2025年美国社会所经历的真相是,一个本可以为彼此提供帮助的社会,却因为“他们不配”和“我什么都没得到,凭什么他们应该得到”之类的理由而拒绝伸出援手。这里的“他们”指的是一些“他人”,他们似乎不配被称为人类。 一个更有力的论点并非我们不欠任何人任何东西,而是我们所欠的是有条件的。有些人将“核心家庭”视为这种条件,另一些人则认为是“美国公民”或“公共服务人员”。毕竟,一个人不可能对所有人都负有所有义务。一个人能够关怀的能力需要设定限制,这些限制虽属合理,但终究是限制。
这并非不近人情。没有人能够以有意义且具体的方式关怀世界上八十亿人口。然而,我们确实共同生活在这个星球上,无论我们是否选择承认,我们都已深深地交织在一起。 即便你选择了一种尽可能与世隔绝的生活方式,远离家人,并“脱离主流”,居住在远离他人的地方,你依然会受到他人决定的影响。选择隔离之地,也只能在那些你选择不开发或更倾向于保护的区域中进行。你所掌握的每一项生存技能,至少都源于一个来源——无论是书本还是另一个人,而这些知识的积累,是无数人付出努力、甚至血的代价才得以发展起来的。
你使用发电机发电吗?它是在工厂里制造的,按照商业规格和最低监管要求设计。除非它是由你亲手砍伐的木材驱动,否则它所消耗的燃料,是你个人无法独立完成从开采、提炼到分销任何一个环节的。 你是在寻找食物吗?即便你亲手制作了弓,其设计也凝聚了数千年前人类在种植第一株作物之前,无数次迭代的智慧结晶。如果你正在耕种,那么几乎可以肯定,你手中的每一粒种子,都源于人类长期干预的成果,旨在培育出更优质、更具生命力的作物。
好吧,好吧,我明白了。没有人是一座孤岛。你或许会反驳说,这一切固然属实,但这些都不是你所要求的,也不是为你量身定制的。你并没有选择来到这个世界,并且可以选择只接受生存必需。你的选择不会影响任何人。
但事实并非如此。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无论大小,我们所做的每一个行动,甚至每一个念头,都会激起涟漪,即使微不足道。而在足够长的时间尺度下,即便是涟漪,也可能演变成滔天巨浪。 即便我们选择独善其身,于人世间孤身生活、孑然离世,我们赖以维生的资源也早已悄然牵动着周遭世界的脉搏。每一次呼吸,每一次生存的消耗,都在改变着当地的生态平衡,都在为大气层添上一笔碳的痕迹。更何况,你所做出的每一个决定,你所书写的关于自己的每一个故事,都可能被他人偶然瞥见,并深刻影响他们与这个世界互动的方式。在咽下最后一口气、融入他人的记忆,或是以物质的形态留在我们曾触碰过的世界中之前,我们始终无法真正摆脱这一切的羁绊。
既然我们的行动、言语、选择乃至思想都必然伴随着后果,那么责任也就如影随形。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承认,我们所做的一切,终将对某些事物,抑或是某些人,产生不可磨灭的影响。 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借鉴一位颇负盛名的道德哲学家的思想。尽管在他所处的时代,人们或许称他为约瑟之子耶稣(抑或并非如此,我们并无第一手的文字记载),但我们熟知他便是基督耶稣。抛开他更为宏大的教义不谈,他关于与人共处的格言,可以被精炼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至此,我们梳理出以下几点:对个体孤立生存可能性的细致探讨,以及耶稣、佛陀以及无数先贤所共有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人类一以贯之的格言。从中,我们可以得出:
- 无人能够孤立存在。
- 我们的行为会对他人产生影响,因此,
- 他人的行为亦会反作用于我们。
-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即互惠法则,为我们在这种相互依存的环境下如何生活指明了方向。
- 正如我们不愿他人强加于我们不希望发生之事,我们亦不应如此对待他人。 按照互惠原则,我们不应将自己不愿承受之事施于他人。
进一步而言,我们亦可采纳积极的准则:力行我们期望他人施予我们的善举。
回到我们的话题,至少我们不应做出自己不希望他人施加于自己的事。而倘若他人能为我们做到我们所期盼之事,那无疑是件幸事。正如一位美国中西部的母亲可能会说的:“你又怎会知道呢?”或许我们也应尽力为他们做到他们所期盼之事。
呼,这听起来似乎浅显易懂,但我认为有必要在此提及。我们彼此之间存在亏欠。那么,我们究竟亏欠什么呢?
这个问题已困扰哲学家数个世纪,我并非在开辟新的疆域。T. M. Scanlon 在其题为
欢迎随时发表您的看法,
《我们彼此亏欠什么》的里程碑式著作中,已对此问题进行了极为精妙的探讨(至少在道德哲学界是如此)。 他以严谨的学术框架,深入探讨了这一思想,旨在确立约束人际关系的道德义务,由此引申出斯坎伦的契约主义。
那么,他的结论是什么呢?我首先要说,你应当阅读《我们彼此亏欠什么》,或者至少观看情景喜剧《善地》的全部四季,因为他的思想在剧中有所体现。此外,我并非契约主义领域的权威。尽管如此,我认为可以将其概括如下:
- 核心论点: 如果某种行为在特定情境下,被一套行为准则所禁止,而这套准则,任何人都无法合理地拒绝将其作为知情、自愿的普遍协议的基础,那么该行为就是错误的。这一定义了道德上的错误,并非基于行为的结果,而是基于该行为是否能以他人无法合理*拒绝的原则来证明其正当性。(*此处存疑) · 拒绝那些“不合理”的原则,即为了给他人带来微小的益处,却给某人施加了过度的或不公平的负担。整个道德体系的建立,都依赖于找到这种平衡。
这句表述或许不够精炼,但与道德相关的探讨,精炼并非首要的美德。
· 道德的本质在于,以一种任何人都可以合理接受的方式与他人共处,这种共处以尊重、可辩护性以及承认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价值中心为基础。
这样的表述要好得多。虽然它可能不适合印在T恤的正面,但至少可以印在背面。深入思考后,我非常赞同作者在某些原则上的观点。将道德建立在尊重和承认所有人都因其自身价值而具有价值的基础上,这一点切中要害。
他还否定了功利主义,即在试图最大化净收益时,“结果证明手段是正当的”这种观点。我对此表示赞同。你不能因为给许多人带来一点点好处,就合理化对一个人造成巨大伤害的行为。 斯坎伦进一步阐释了这一道德框架的“非”之处。它并非法律条文,也不是个体独立存在的最佳状态,更非宗教的强制要求。它仅仅是那些无法被合理拒绝的原则。
简而言之,斯坎伦认为,我们之间亏欠的,正是那些无法被合理拒绝的义务。当然,这其中蕴含着远比这更为复杂的思辨,但这已然可以视为一个精炼的总结。
太好了,斯坎伦似乎已经为“我们彼此亏欠什么”这一问题给出了答案,并定义了其内涵,而我的观点似乎也与他契合。我为何还要舍近求远?只需将此原则印在名片上,每当我需要为模糊的道德互动寻找指引时,便可信手拈来,轻松应对。
不妨来做一个小小的测试。时值清晨,我路过星巴克,正准备上班,顺道买杯咖啡和一份早餐三明治。这时,我看到一位流浪者坐在店外。我口袋里揣着一百美元现金。我是否应该将这笔钱全数给予他? 他并未向我索取财物,也未与我进行任何形式的互动。然而,我曾在此处见过他,也曾看见他栖身于街对面公园的角落。不妨让我们从斯坎伦的视角来审视这一议题。
这个人从未向我提出任何要求,除非我主动,否则我们之间并无任何个人层面的交集。我是否能为自己的视而不见,为继续过自己的生活而找寻借口?
让我们来确立一个道德原则:我可以从一个人身边漠然走过,而不施舍我口袋里的分毫,然后继续自己的生活,因为我并无义务给予他任何东西。我认为,任何理性之人对此都不会提出异议。
然而,关键在于,我们究竟彼此亏欠些什么?或者更精确地说,我亏欠这个人什么?
我大可以袖手旁观。没有人会断言,我从道德上必须遵循“将我口袋里的所有财物都交给他”的原则。 然而,从我道德账簿的明细来看,与这个人擦肩而过,我确实造成了伤害。这是一种冷漠的伤害。我看见了他。我无法装作视而不见,即便我是我冷漠的唯一见证者。
但我并非唯一见证者。他也是。他见证了我假装视而不见。他看见了我对他困境的漠视。他或许不知道我本可以做什么。但他知道我究竟做了什么。什么也没做。
而我,却清楚我本可以做什么。我知道我轻易就能从口袋里掏出那100美元。我拥有一份稳定且收入不错的工作,这份工作的内容很可能只是玩手机,而非履行我的职责。我不到两小时就能赚回这100美元。通过忽视这个人以及他的困境,哪怕是以最微不足道的方式,我也侵蚀了他作为一个人尊严中那微小却并非无关紧要的部分。而且,我对此心知肚明。
我究竟欠这个人什么? 账本上,我记录着自己的冷漠。当时,我可能只是觉得有些不自在。然而,一旦我选择了冷漠,下一次再面对类似情况时,我便会更容易忽视内心的不适。而且,这样的“下次”总会不期而遇。
或许,另一个人也像我一样,走进同一家星巴克,在上班途中停下来,为自己买些食物和咖啡。我们同样没有互相打招呼。但我的一个善举,或许能启发那个人,促使他们反思自己能做些什么,从而在细微之处,将他们引向另一条道路。
“这未免太令人不知所措了!”我仿佛听到了你的声音。“没有人能时刻顾及这一切。人们忙于生存,已是竭尽全力!斯坎伦说得没错,我并没有义务这样做,我可以继续前行,以免错过九点的全体会议。这简直太荒谬了。” 我十九岁时在军队服役。在安吉尔去世前几个月,我完成了基础训练。我每周都会从新的驻地给她打电话。在每次二十分钟的通话中,我总是滔滔不绝地讲述我的生活。
我买了一辆车。我交了新朋友。我练习射击、投掷手榴弹。我参加行军、跑步。我兴致勃勃地分享我经历的一切。然而,我从未问过安吉尔的生活。
我认为,一个理性的人可以合理地拒绝“与兄弟姐妹通话时,必须询问他们的近况”这一道德原则。他们或许会辩称,我应该这样做,但这并非一种道德义务。毕竟,我的生活中发生了太多新鲜事。而且,我每周都给她打电话。我本可以更主动地关心她,但这并非道德上的瑕疵。
然而,她没有告诉我的是,正因为我从未主动询问,她当时正饱受头痛的折磨,甚至会昏厥,并且已经接受了核磁共振检查。 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周,当她焦急地等待结果时,她质问我是否在乎。她质疑,那个从出生起就陪伴她的人,是否真的 爱 她。甚至在出生之前。在她离世前,我未能消除她的疑虑。在她离世后……我亦永远无法改变这一切。
维护道德的账本,又要求我们付出什么?它又如何回应“我们彼此亏欠什么”这一疑问?
我们彼此亏欠的是“见证”。是视对方为一个完整的人,是看见我们的言行(以及不作为)如何深刻地影响着彼此。是铭记,是学习。
好的,铭记。但每一个细微之处?每一次轻微的冒犯,无论真实与否?这未免太过沉重。账本又该如何指引我们行动?这对于星巴克里那位无家可归者,又意味着什么?
在我们所做的每一个选择中,我们都在激起涟漪。账本要求我们去见证这些涟漪。当这些选择来临时,我们便应用所学。我们明白自己能做什么。但更重要的是,我们也清楚自己不能做什么。 我们以同理心去体察自己的选择将如何影响他人,以理性去审视自己何为能为、何为不能为。
我曾亲眼见证过什么?庆幸的是,我曾亲眼目睹,也有人曾关注着我。在我还是个沉溺于创伤与愤怒的少年时,就有人向我伸出了援手。他们竭尽所能地帮助我,敞开了他们的钱包、家门,甚至他们的生活。这一切都源于他们的自发。即使是最微小的善举,在当时以及如今,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至于星巴克里那位男士,斯坎伦的契约论告诉我,即便我拒绝将口袋里的钱递给他,也并非不合情理。账本也印证了我并无义务为他做任何事,但它却清晰地记录下了一桩伤害的发生。
运用同理心,我深知一次不期而遇的善举能够带来多大的改变。我明白,我可以赋予他人尊严,可以告诉他,他被看见了,他并未被遗忘。 凭借理性,我知道这 100 美元对我而言微不足道,但对他来说,其意义可能非凡。我深知我并无义务,但也清楚我所能带来的益处,远超我记录下的那点微小“损失”。
他欠我什么?分文未欠。更不用说感激。他也没有义务必须明智地花用这笔钱。他甚至不必接受。
我欠他什么?我欠他一切。
这不是为了安琪的赎罪,不是圣人行径,也非标榜美德。这是我毕生所学,是我选择理解自身涟漪如何触及世界,并以此构建道德框架。我并非通过研读经典,而是通过在广阔天地中,日复一日地回应这些问题。我并非应对我所认为世界“应有”的样子,而是接受世界“本有”的样貌。这是一种与我唯一能掌控之物——我自身——的和解。这便是人文主义的构建之道。 我擦肩而过,走向星巴克的大门。店内一片宁静,除了忙碌的店员,别无他人,他们专注于各自的工作,在我踏入的那一刻,我并未引起他们的注意。
星巴克门上的铃铛近在咫尺,但我的脑海中,一本无形的账本已经翻开,我那冷漠的伤害被悄然记录。我停下了脚步。
十几种看似合理的借口涌上心头。风险显而易见,他可能会将这笔钱挥霍一空,对自己造成伤害。当地的商家或许会称之为“纵容”。依照斯坎伦的理论框架,我并没有任何强制性的义务。
然而,那本账本要求另一种计算方式。我深知,一次意想不到的善举能带来多么深远的影响。我清楚,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非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且,我明白,对我而言,这笔钱微不足道,而对他来说,却可能改变一切。潜在的益处,远远超过了我那漠不关心的冷漠所造成的确定性伤害。 我转过身。他望着我,我掏出钱包,手中柔软的纸币显得如此微不足道。我将它们递给了他,一百美元。我微笑着转身离开。
他看着,数了数,随即跳了起来,睁大了眼睛,似乎明白了什么。他手忙脚乱地站起身,抗议道:“不,伙计,我不能收下。”
“这是你的,”我说。
他结结巴巴地道谢,并问我是否有什么可以为我做的来回报。
“你不用放在心上。你什么都不用做,”我告诉他。“但如果你能,请记住这一点,并在别人需要时,也施予他人一份善意。”
没有债务,只有善意的馈赠。账本将见证并记录这一切。
如果你觉得这段经历颇有触动,如果你曾走过某个人身边,思考“看见他们”究竟意味着什么,或者你曾问自己,那些悲伤与愧疚应该促使你建立怎样的联系,我希望你能继续与我一同探索。 这是“账本伦理学”与“建筑人文主义”系列文章中的一篇,该系列旨在探讨一种道德哲学,其核心在于“在场”的意义、见证的力量,以及我们对自身行为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所应承担的责任。
来源:TrueReddit 原文地址:https://anthonyscurtis.com/what-we-owe-each-oth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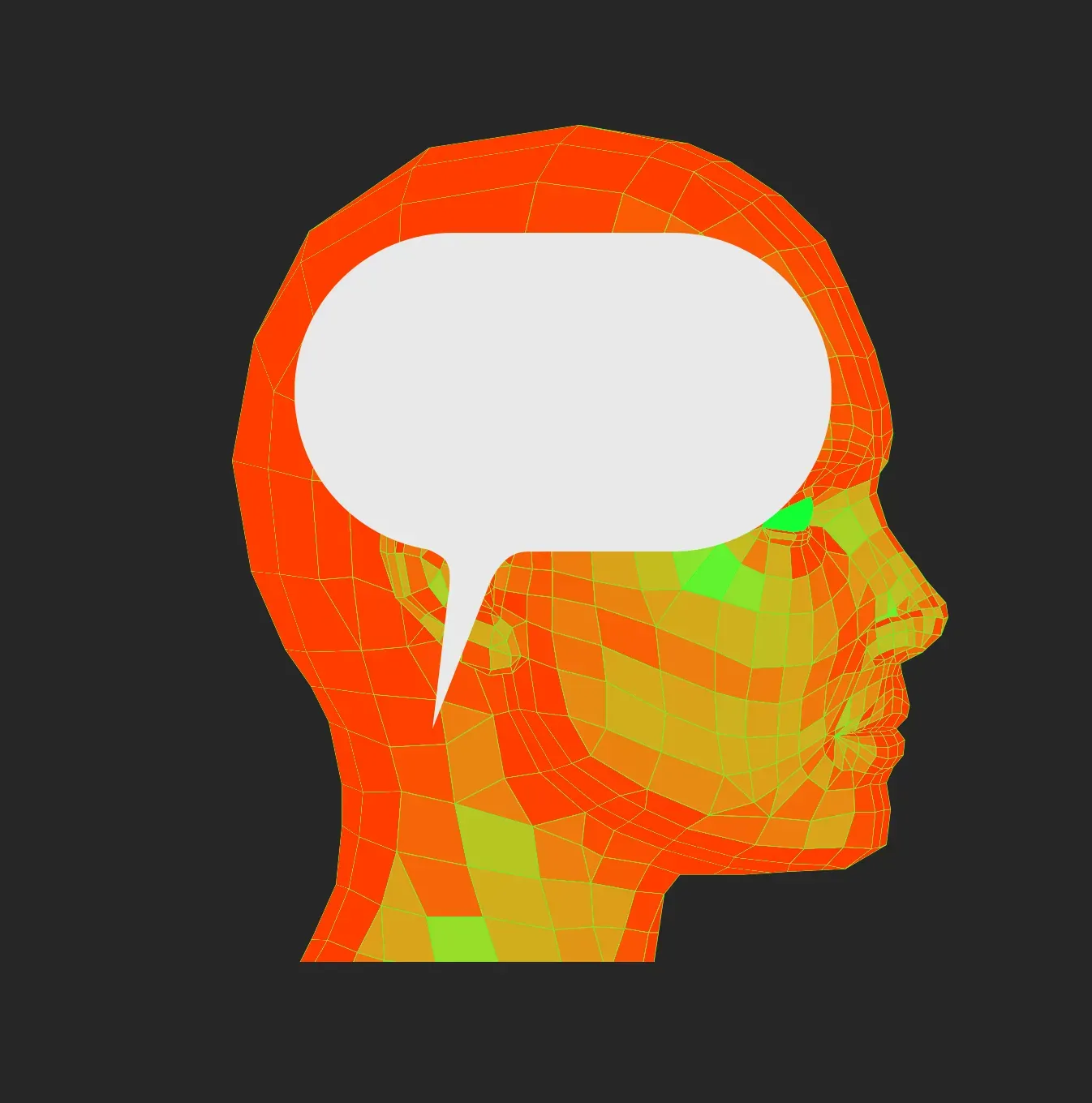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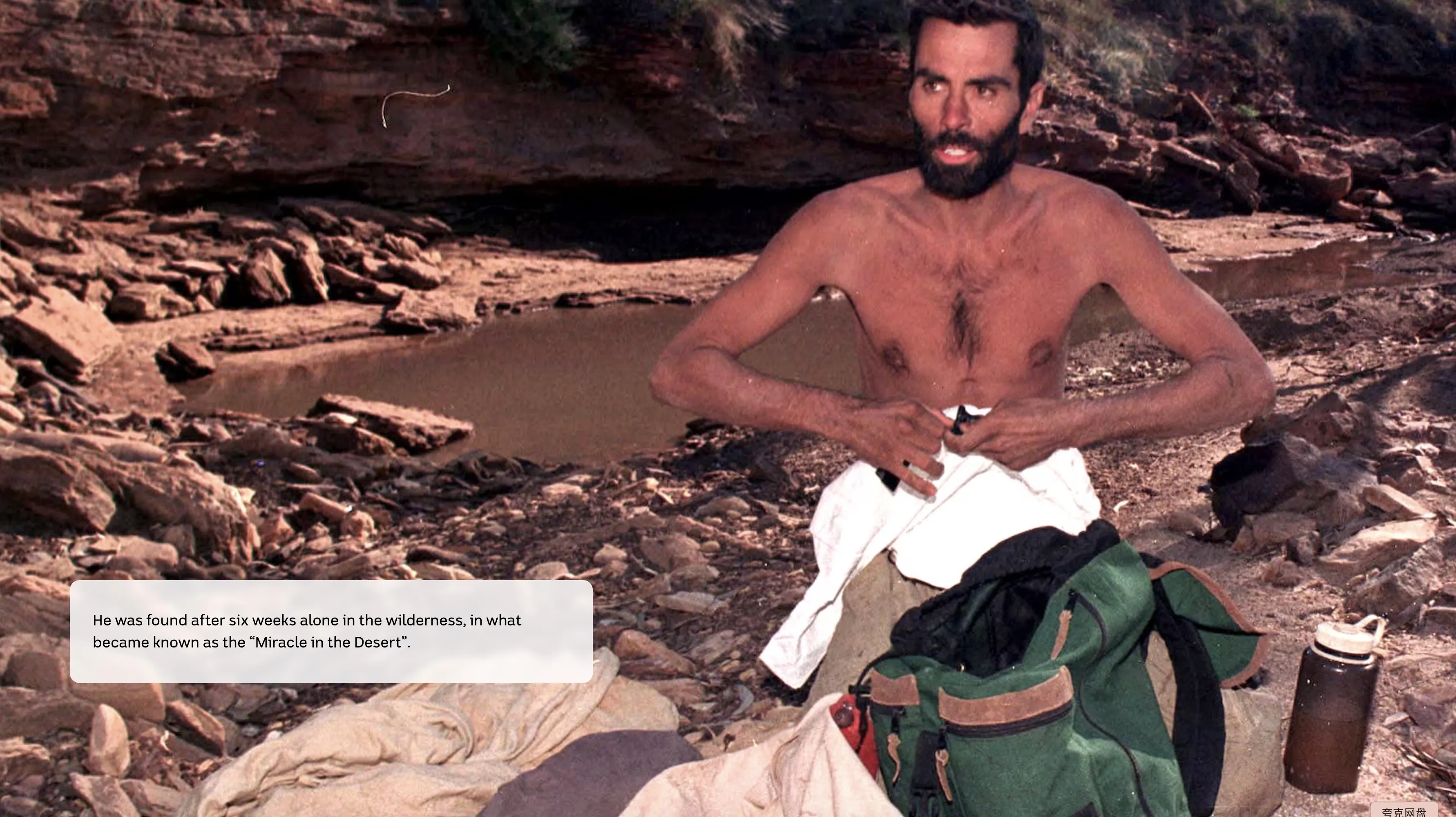
评论 (0)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