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Westenberg

两天前,我删除了所有。
我清空了 Obsidian 里的每一条笔记:那些不成形、不成篇的原子化想法,每一张 Zettelkasten 卡片,每一幅精心勾连的概念图。我删除了 2015 年以来同步过的每一则 Apple Note,划下高亮的每一句引言,以及那些我曾借用、改造、抑或胡乱拼凑过的生产力系统里,林林总总的待办清单。一切都消失了,在短短几秒钟内,灰飞烟灭。
随之而来的,是如释重负。
曾经的喧嚣,被一种令人慰藉的宁静所取代。
多年来,我汲汲于构建一个技术专家和“生活黑客”(life hacker)们口中的“第二大脑”。它的信条是:捕获一切,遗忘便无可能。将你的思想储存在一个庞大且能无限回溯的网状知识库中,它便能在你意识到问题之前,就为你奉上答案。它承诺带来清晰的思路、一切尽在掌握的感觉,以及为你的思维加上杠杆,等等等等。
但随着时间推移,我的“第二大脑”变成了一座陵墓。一座尘封的陵墓,堆满了我过去的自我、过时的兴趣、陈旧的执念,如地质层般层层堆积。它非但没有加速我的思考,反而开始代替我思考。它非但没有辅助我记忆,反而把我的好奇心冻结在僵化的分类里。
于是……我把这整座陵墓夷为了平地。
我戒酒六年了。这样的里程碑,会改变一个人对时间的感知。它在生命中划出了一道“之前”与“之后”的分界线,并敦促你——起初温和,而后执着地——去盘点过往。几周前,在回顾戒酒历程时,我翻开了我的数字档案,浏览着那些旧笔记、旧目标、旧的思维框架——那些我曾奉为圭臬的东西。一套套系统,层层堆叠。我曾向未来的自己许下诺言,仿佛未来的我,只是一个等待升级的操作系统。
读着这些思想的残骸,我感到胸口一阵窒息。不是悲伤,也非怀旧——而是一种关乎存在的滞后感。我能看到,过去每一个版本的我,都曾那么殚精竭虑,试图为自己规划出一条通往“更好”的路线图。 但那些真正让我清醒、伴我度过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艰难年头的体验,却无一在这些笔记之中。
我恍然大悟:领我至此的旧路,已无法带我到想去的远方。
“全盘捕获”的承诺
现代个人知识管理(PKM)运动,其根源可追溯至一种近乎学术的痴迷——痴迷于系统论、卢曼的卡片盒笔记法(Zettelkasten),以及硅谷那套将生产力奉为圭臬的迷思。 Roam Research 将双向链接推上了神坛,Obsidian 则让这股狂热成功“出圈”。与之相关的神话也愈演愈烈:你不是在记笔记,你是在构建一张意义之网,一座连博尔赫斯都会为之赞叹的图书馆。
但博尔赫斯早已洞悉这种“总体系统”的代价。在他的《巴别塔图书馆》中,他构想了一座藏有世间一切可能书籍的无限图书馆。馆藏之中,既有完美的真理,也有完美的呓语。那些被诅咒在此间永世游荡的管理员们,最终都陷入了绝望、疯狂和虚无主义的深渊。地图吞噬了疆域。
PKM 系统承诺带来秩序,但它们往往催生出一种抽象的混乱。我向知识库里倾倒的内容越多,我的感受就越贫瘠。一句引言激发一个想法,我便剪切、标记、链接——然后继续前行。但那个想法从未被付诸实践,它只是被“储存”了起来。如同被真空密封却从未下咽的食物,其营养也随之流失。
更糟的是,这套架构开始塑造我的注意力。我开始为了摘录而阅读,为了总结而聆听,为了归档而思考。每一次体验都沦为了素材。我停止了好奇,开始了处理。
对大脑的错误隐喻
“第二大脑”这个比喻,既宏大,又在生物学上站不住脚。人类的记忆并非一个档案馆,它是联想的、具身的、情境化且情绪化的。我们不在文件夹里思考,也不靠反向链接来检索意义。我们的思想是即兴的,它们甚至会刻意遗忘。
在认知演化理论中,梅林·唐纳德(Merlin Donald)提出,人类智力的飞跃并非源于静态的记忆存储,而是源于外部符号表征:语言、手势、文字等工具,使我们得以演练、分享和重塑思想。文化,成了一套集体记忆系统——其目的不是为了存档知识,而是为了让知识在不断的重演和再加工中,保持鲜活。
在试图记住一切的过程中,我已然将反思这一行为外包了出去。我不再重温旧想,也不再审视它们,只是将它们归档,并信赖这套结构。但结构不等于思考,标签不等于洞见。一个从未被重温的想法,与一个从未有过的想法,别无二致。
工具的暴政
每一种工具,都会改变使用者的手的形状。
Obsidian 是一款杰出的软件,我由衷地喜爱它。但凡事若无节制,它也会成为一个陷阱。层层嵌套的 Markdown 文件,追踪你产出的插件,以及那个暗示你无所不知的图谱视图。看着你的笔记交织成一片星海,会产生一种掌控一切的错觉。但星座只是投影,它们讲述故事,却不保证理解。
起初,我以为我在解决遗忘的问题。后来,我以为我在解决整合的问题。直到最后我才意识到,我亲手制造了一个新问题:智识上的拖延。我的系统越是庞大,我就越是把思考的重任——那些整理、标记、提炼的苦工——推给未来的自己。
然而,那个我所寄望的自己,却从未出现。
未读的焦虑
未读的书籍、文章和博客会带来负罪感,但未读的“待读清单”,则带来一种别样的焦虑。我的阅读清单早已变成一座象征着虚幻智慧的图腾,一座祭坛,供奉着那个“假如我读完所有这些,我就能成为”的理想自我。
当我删除那份清单时,我并未失去任何真实之物。我想读什么,我心里清楚。我注意力的轮廓,我自己明白。我不需要一个存有七千个条目的数据库,来证明我的品味或抱负。
这折射出一种更深层的心理谬误:我们相信,为目标命名,就离实现更近了一步;储存一个想法,就意味着理解了它;归档一个事实,就获得了运用它的权利。
这无异于将生产力当作一种表演。它是现代知识工作者不安全感的集中体现:害怕掉队、害怕遗忘、害怕落伍。但掉什么队呢?信息流?热点话题?还是模因(meme)的生命周期?
求知没有终点线,只有此时此刻的起跑线。
以毁灭为设计
尼采烧掉了他的早期手稿,米开朗基罗销毁了他的草图,达芬奇留下了数千页未竟之作。删除,并非档案管理的失败,而是一种主权的宣示。
在设计中,我们称“减法”为“精炼”。雕塑家剔去一切不属于雕塑的石料,音乐家抹去一切干扰旋律的杂音。但在知识工作中,我们却成了囤积者,将积累奉为圭臬。
但倘若,“删除”才是那更纯粹的修行呢?
我想,我不需要一张标明我读过什么的地图,我想要的是一个能自由阅读当下所需的大脑。我想要一段能优雅地遗忘的记忆。我想要那些能自然而然重新浮现的观点——不是因为我为它们建立了索引,而是因为它们真的举足轻重。
从零开始,是什么感觉?
就像裸泳。轻盈,赤裸,略带脆弱。但前所未有地干净。
我写作,并坦然接受它可能消失。我给书划线,也明白那痕迹终将褪色。我相信,真正重要的东西自会回归,它们会自己找到浮出水面的方式。我不再迷信文字的永恒。
希伯来语中有一个词,“zakhor”,它既指记忆,也指行动。在这一传统里,记忆不是回忆事实,而是履行一种道德责任——通过专注,让过去在当下重现。
我的新系统,简而言之,就是没有系统。我写我所想,删我所弃。我不记录一切,也不试图记录一切。我随心阅读,在对话中思考,在行动中思考,在情境中思考。我不再构建一个第二大脑,我选择活在我的第一大脑里。借用几年前 DHH (37Signals) 对我说过的一句话,我开始只保留一个名为“WHAT”的笔记,里面只记那些我当下非记不可的事。真正重要的东西,总会自己找回来。
我不想管理知识,我想亲历知识。
我依然喜爱 Obsidian,也打算重新使用它。从零开始。但会带着更深刻的审慎与关怀——不再将它当作“第二大脑”,而是我既有大脑的工作台。
对此,我感到了多年未有的兴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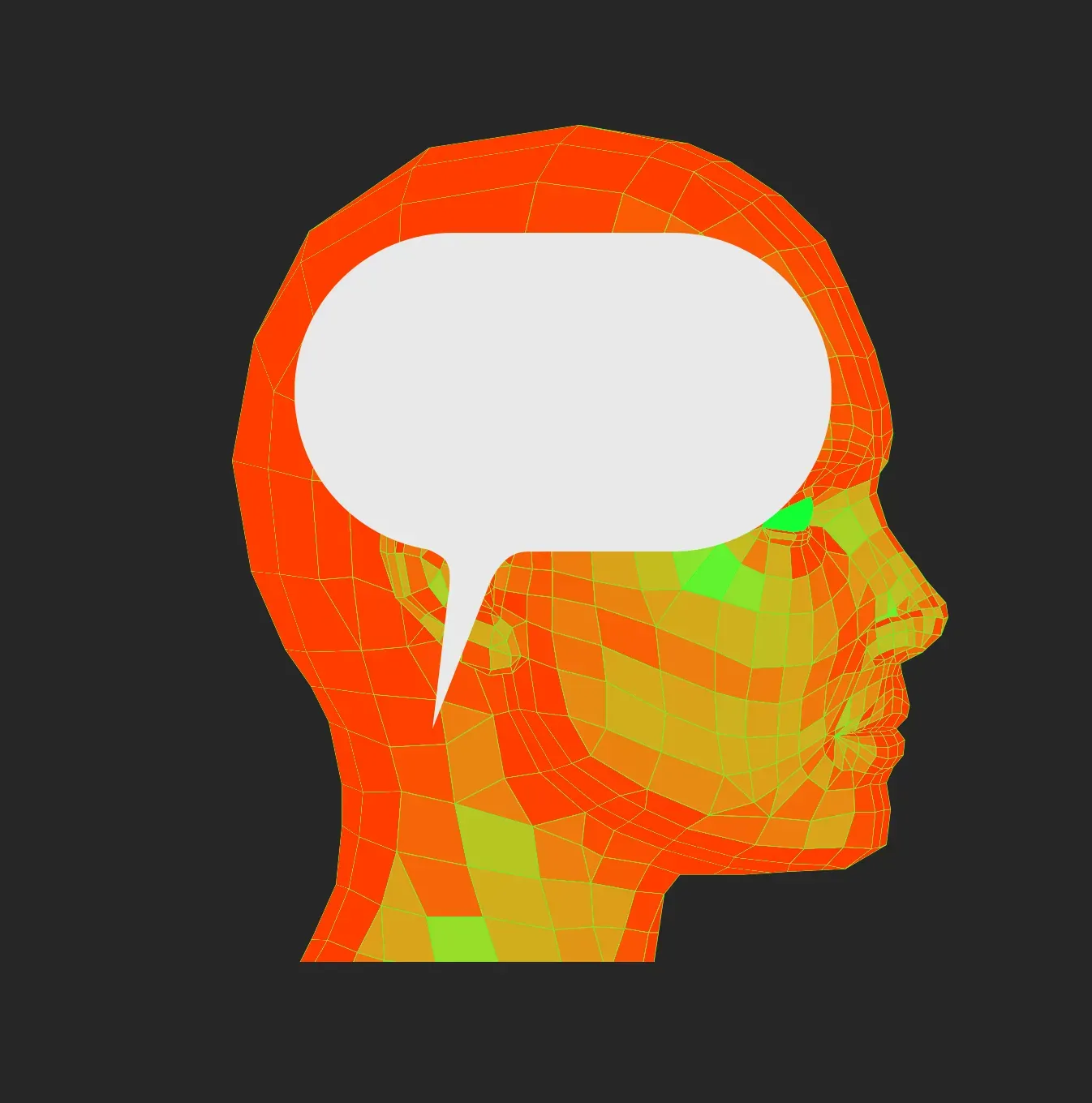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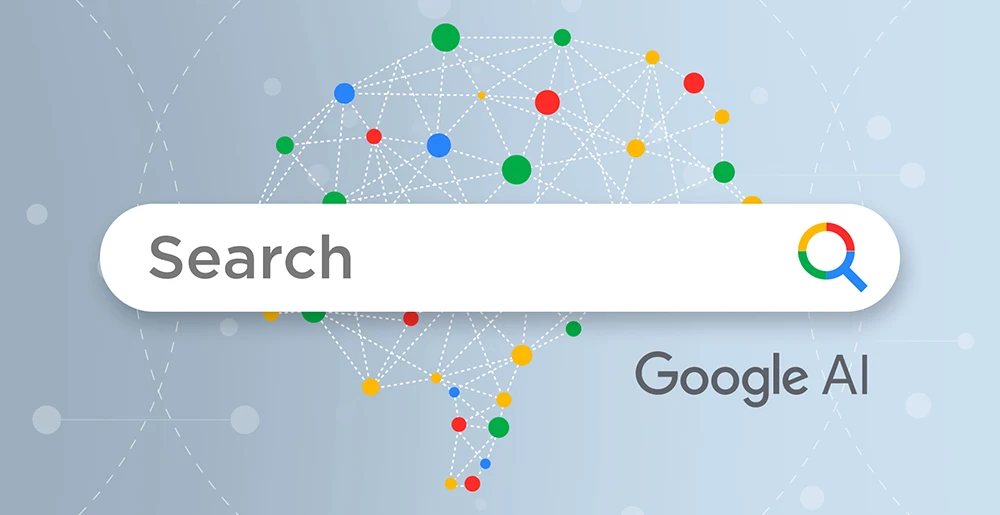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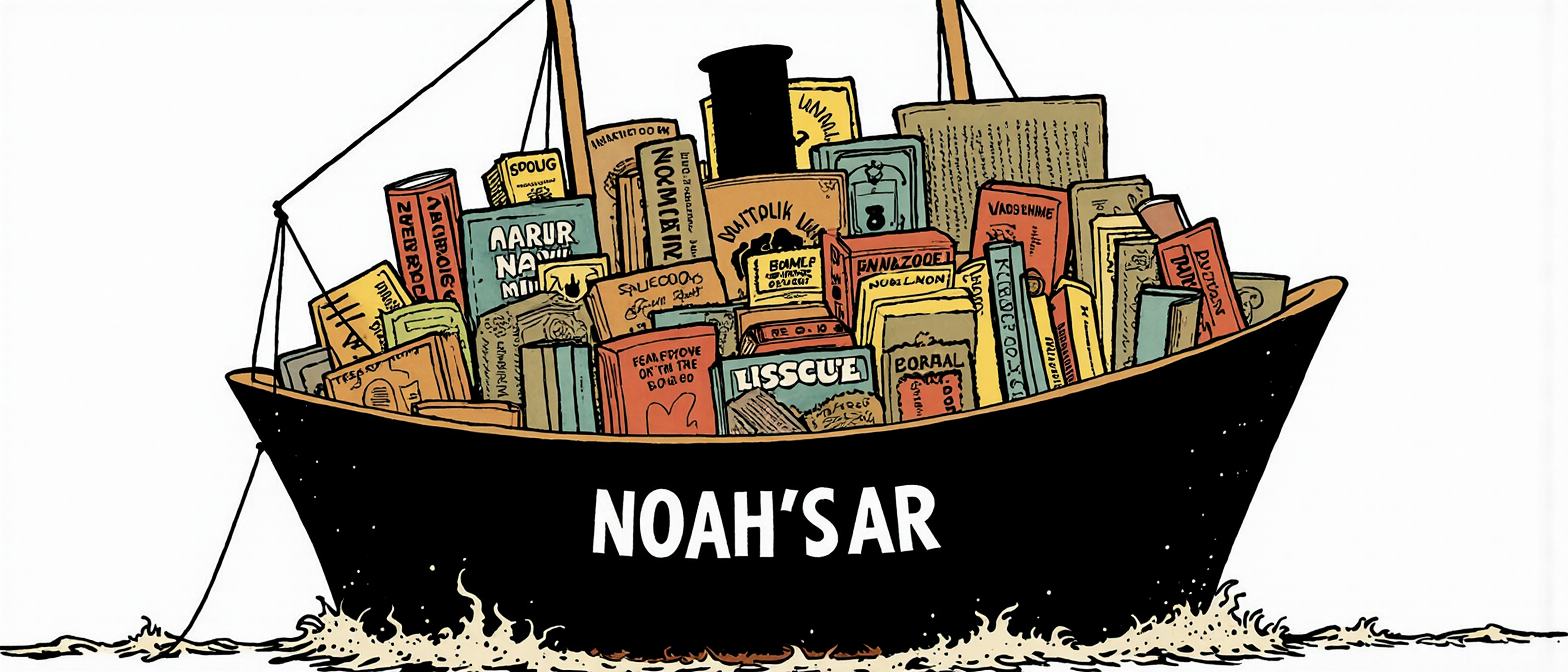
评论 (0)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